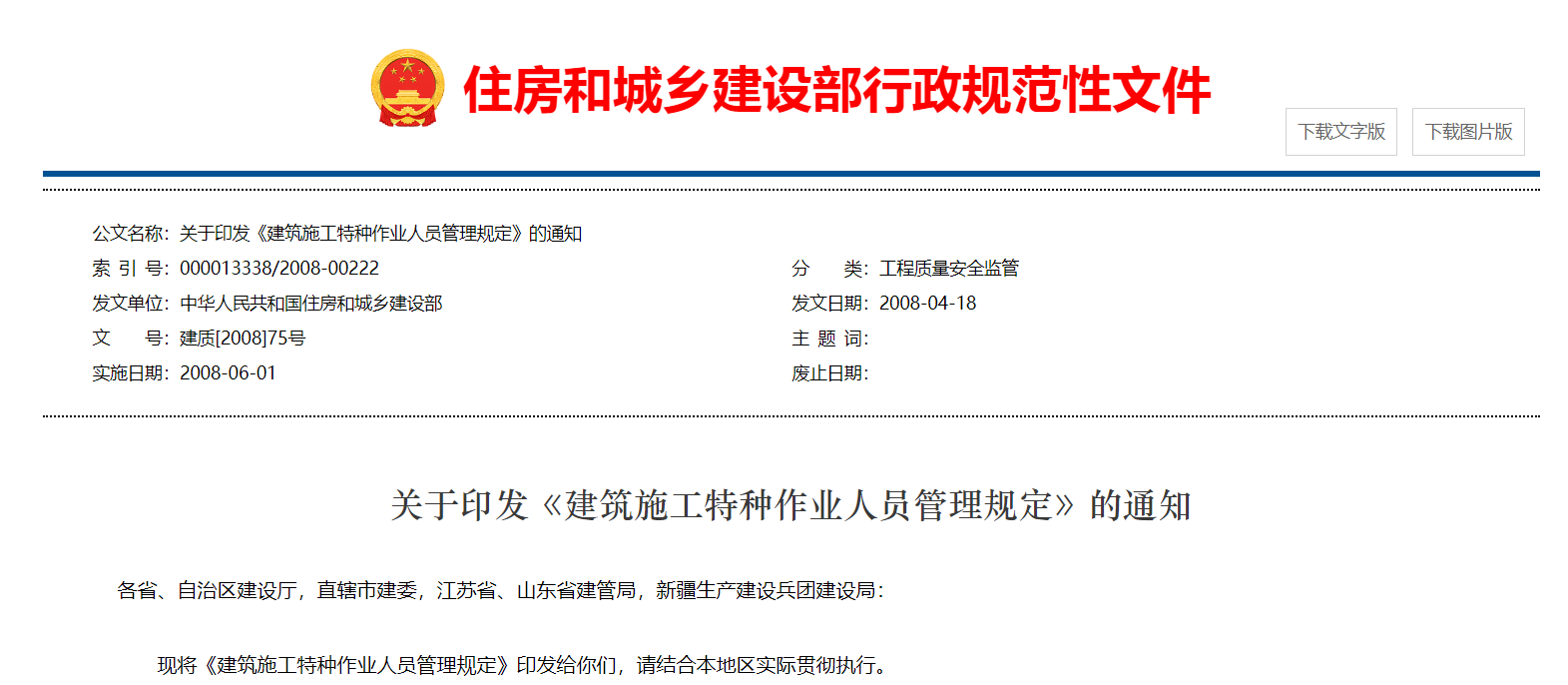读了“不会失业”的土木工程,我三年换了四份工作
本文作者:柴禾,由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(微信公众号:thelivings)

“土木这个专业既不好,其实也好。很辛苦,但是能赚到钱。很乏味,但是能攒下来钱。很折腾,但是不会失业。”

配图 | 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剧照
2021年底,我校土木工程系的同学们在武汉相聚。毕业近3年,原本40余人的班级,准点到场的不过寥寥10多个——还全是仍在读书或者已经转行的,真正从事土木行业的,都不见踪影。 “我们在工地的同学,大概都比较忙,抽不开身。”班长端起酒杯,替他们解释道。 我们没有感到惊讶,只是觥筹交错间颇感可惜。直到聚会进行到一半时,王超突然推门而入,才打破了这场没有“土木人”的土木专业同学会的尴尬——他目前仍活跃于工地,称得上“不忘初心”的优秀代表。 王超当年是我们系的明星人物,学习好,长得帅,个头高,颇讨女孩子喜欢。他毕业后去了一家不错的单位,接连涨薪,这一年听说赚了近30万,是我们班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里最高的,作为普通学校的本科生,他已十分符合“成功”的标准,尤其是符合土木行业的成功标准。 说实话,当初我们大家选这个专业,看重的无非是工作后钱多、稳定,但后来却发现,也不是谁都能端得起这碗饭。我毕业前去修地铁的工地干了2个月,就知道自己吃不了这份苦,找工作时,迅速换了赛道——大多数转行的同学,也都跟我的情况差不多。 而王超,看起来应该是捧稳了这碗饭。 “对不起诸位,我来晚了。工地有些事,坐迟了车。”他一边寒暄一边抱歉。见他风尘仆仆的模样,我想他大概不是专门为聚会而来的。果然,他接着说:“其实我是从甘肃赶来武汉述职,才有机会和大家相聚。” 听到这里,我们方知他已经被破格提拔为项目副经理,暨储备项目经理,不愧“优秀”二字。 一阵稀疏的掌声过后。班长当着各位同学的面举起白酒杯对他说道:“不管怎么说,能来就好,你现在一定是我们班混得最好的了——王总,我们祝贺你,干了它。” 周围起哄起来,王超举起酒杯,神色复杂地笑笑,仰头一下就干了杯里的酒。 然而,这次聚会之后没几个月,我便听说王超辞职了。我很是讶异,便趁他回校做分享时,又约他聚了一次,听他细聊了一下这几年的经历。 以下是他的自述。

我是1997年生人,家在湖北省恩施的农村。 2015年高考结束,我的分数刚够得上一本院校。选专业时,我没多犹豫就报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——土木工程。各种宣传上说,土木工程专业学得到技术,将来赚得到钱,而且“工程师”的名头也特别唬人,可以考证、“挂证”,额外收入不菲,等再“往上”走走,就可以当专家、做评审,甚至自己分包工程,“越老越吃香”。 再说,即便将来不成为像模像样的总工程师、专家、包工头,最低也能有工地上包吃包住、收入稳定增长,这对于出身农村的我而言,是一份切实的保障。所以,对我选择这个专业,父母亲戚都表示满意。 大学新生见面会上,土木学院的副院长给我们放关于中国基建的纪录片。看到在建的港珠澳大桥、重庆来福士摩天大楼时,我十分笃定,自己的前途也会像这些巨无霸工程一样光明。 4年本科时光,我也努力学习了不少力学和造价知识,做过测量实习,参加过全国大学生结构模型大赛,也曾亲手养护半月的砼试块(用于测定混凝土强度的试块),那时,我觉得这个专业有无限的趣味。 我还喜欢上了土木系仅有的几个女生里长得挺好看的一个。大学时不讲究钱,不讲究出身,只讲究外表和成绩,我自觉长相尚可,也一直保持全系前十的绩点,于是就真追上了那个女孩子。她叫小迪,皮肤是闪亮亮的白,身高差我一头,留短发。她是杭州人,家住西湖一公里远。 小迪和学业两者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,但不知哪个更为重要。
土木系的就业方向不算多,大抵是施工单位、房地产企业以及建筑设计院三类。刚毕业的本科生,多半去的是施工单位,一来是最容易进,二来,那里也是老师们常言劝告“施工最能学到技术、最能赚到钱、最能攒下钱”的工作。 2019年临近毕业,我就想着直接去施工单位上班,因为我需要赚钱。有些同学去考研,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,那时我们都笑称:“土木工程有什么好搞学术研究的,尽头无非是当个大学老师。再说本科没有优势,又没出过国,能去什么样的学校当老师?” 在我看来,老老实实工作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不过,读书这4年,土木工程行业对于 “基建狂魔”的吹捧愈来愈少,“房住不炒”的声音则在渐渐增多。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兄师姐们也在逐步离开,常常能听到一些诸如“谁谁谁提桶跑路了”的消息。虽然这都是些不好的信号,但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专业,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,再者,我想毕竟中国幅员辽阔,还有不少地方等着我们土木人的建设呀,我仍旧不乏信心。 我在秋招季收到了不下5份offer,有的是进去走两圈,蹲起两下,再走两圈,就会有工作。更有XX隧道集团,上来先发4万块钱现金,当场签约,面试官说可以拿这钱带家里人旅旅游,给家人买些礼物,然后不忘提醒:“但如果5年内离职,需要全款退回,并按银行的年化标准支付一定利息。” 我听了就有些害怕,怕从此我这人等于完全卖给了他们,再也见不到家里人。更怕抗不过两年,回头苦了自己,亏了利息,没了工作。我拒绝了那沓红彤彤的人民币,心里绝不认同一个本科土木人的身份只值区区4万块。 与此同时,我还收到了驻非洲和中东的施工单位邀请,比国内offer高五六万,赚的是美元,能额外再吃一个汇率的便宜。不过我也拒绝了,——国际新闻看得太多,在外怕有莫名的危险。 经过深思,我最后选择去了世界500强前几名的某建某局。他们号称自己为“天下第一局”,薪资高出普通单位好几万,每月有探亲假,报销路费,晋升渠道看起来也很清晰。当然,好单位的要求也高得多,面试了3轮,淘汰了一大批人。最后,包括我在内,我们系只有2人拿到了这个局的offer。 拿到offer让我甚是自豪,当时唯一让我难受的是小迪找不到相关的工作。她成绩一般,加上性别原因,岗位很难找,用人单位看到她细皮嫩肉更加不敢要。这种现象也算不上性别歧视,因为那些工作实际上确实不适合女生,我想让她瞧瞧有没有什么机关单位可去,却也没有合适的。 她给我庆贺了一番后,听了家里的话,学习雅思,打算去国外念个别的专业的硕士,环境一类的,随后再回国工作。没毕业之前,她就收到了英格兰一所学校的offer,排名靠前,周期2年。 我略微有些失意。我俩做了约定,说了些等待和承诺一类的话,没到分手的程度,我祝福的话更多些。

2019年7月,我正式入职,第一个任务是修路,云贵高速,工地在偏僻的山区,风光旖旎。当地有几十个标段属于我们单位,每个标段10到20公里,平均造价约莫有20亿,周围还有大大小小“各建各局”和我们多线并进。 在施工单位,有个大致的“升级打怪”的顺序——测量员、施工技术员、副部长、正部长、生产经理、项目副经理、项目经理,我们这里也差不多,我也是要先从测量员做起。 测量员,顾名思义,施工前放线测量地面的标高,施工中复核检验数据,施工后监控地面沉降,时时记录整理,再用电脑计算绘图。说起来麻烦,其实并不需要自己动脑,将数据导入一些软件即可。一套流程下来,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测绘专业的人,事情简单,却很枯燥。 带我的“师父”是个80后,但沧桑得像个70后。他安慰我说,新人总要做半年、一年的测量才能转去施工,哪怕是现在的庄总(我们当时的项目总经理),也是从测量做起来的,熬了10来年,才到现在这个位置。 其实我不太认同硬熬资历的鬼话,想问他为何至今仍是测量员,但怕他难堪,便没开口——细细想来,既然有成功的人,必然有失败的人。 可没多久,他就“原形毕露”,安慰我的话渐渐变成抱怨各种不公的话,后又扩大为对整个公司乃至行业的诋毁:“食堂阿姨是他表姑,总工是他侄子,那个油水大的活,故意分包出去吃回扣,全都靠关系的,这里也好,总部也好,都是靠关系的——他奶奶的,下辈子绝对不干工程!” 我问他为何不跳槽,他才又改了口:“这里管吃管住,能存住钱,家里还有老婆孩子,不得不图个安稳。再说了,在哪儿都要靠关系。” 我抱了几个月测量用的水平仪,基本都和我的搭档杜晖一起干活,他拿标尺,我拿仪器。杜晖来自河北农村,听说家境清贫,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弟弟。他毕业于专科学校,虽和我做一样的事,工资却少一半,也没有正式编制。我俩几乎同时入职,所以结成了吃苦吃肉的伙伴。我俩虽说身处底层,却兢兢业业,都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成为项目总经理。不同的是,我的第一步是转成施工技术员,他的第一步则是转为正式编制。
工地的饮食条件不错,顿顿好几个荤菜,主食可以选面条、米饭、馒头、红薯。人一累,吃得也多,加上在项目上时常喝酒,我比以前胖了不少。工作之余,我起得早,睡得晚,晒得黑。 一期标段即将结束时,项目经理给大家放了2天假,路途太远,回家并不现实,于是我们搞了活动,约隔壁单位打篮球——他们负责的是紧挨我们的标段。 许久不运动,我上场打了一会儿就体力不支,被大家嘲弄了一番,杜晖说:“你这个样子,女朋友怕是也快分手了。”“去你妈的。”我骂了这小子一嘴,随后下了场,让别的同事上场替我打一会儿。 场下休息时,隔壁单位的一个兄弟走过来,喊我名字:“王超,王超。”我愣了一下,他又喊道:“是我啊!” 天色有点黑,篮球场的灯又暗,我实在认不出来。一直等他近到眼前了,我才看清楚,原来是陈鑫,我大学“隔壁的隔壁”的室友,一个系的,先前读书时不是太熟,只记得是江西人,成绩吊车尾,挂科不少。他以前是个较瘦较白的小个子,现在也变得像碳一样黑,肚子圆鼓鼓的,像怀了孕。 “抽烟?”他随即掏出了一包利群,动作自然连贯。 “不会哈。”我推脱了一下。 他有点惊讶:“还没学会?” “没有,学会喝酒了。” “等会儿整两杯去。”他提议。 即便再不熟悉的同学,哪怕曾经有过矛盾,毕业后在荒郊野外相遇,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,拥抱在一起感觉,仿佛胜过拥抱女朋友。打完篮球,我俩约去宿舍,在住宿区的临时超市里买了一些真空包装的鸡爪、鸭腿、花生米、白酒。酒是小瓶的郎酒,酱香型,一人3瓶,半斤多。这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主动喝酒,我们一边吃一边喝,怀念完大学生涯,接着就谈到了当下。 “你们单位发工资可准时?”他问我。 “准时。”我答道。 “唉,我们可就不行了。”他摇摇头。 “什么意思?” “我们公司是小公司,从我7月份毕业到现在只发了1个月的工资,现在拖了快4个月了。”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。 “啊?!”我颇为惊愕,难以想象。 “现在抽烟的钱都是花我以前存的积蓄,我每天还得给工人、吊车师傅发烟。” “怎么?还要讨好他们?” “我们单位给工人开的工资低,有时还不及时,所以不太听话,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活了。唉!” “那么惨啊。” “可不是,现在我每天抽一包烟,得给工人发出去半包,这样下去,一点钱都没了。”幸好工地吃住不花钱,不然他早崩溃了。 “要不你试试换个公司,反正我们这行,也好找。”我安慰他说。 “唉,咱们这行,在哪儿干不是这样?”他摇摇头,呷了一口酒。 这话和我“师父”的口吻有几分相似,陈鑫像是已被老土木人洗了脑。当时我虽同情他的遭遇,却不能感同身受。

小迪在2019年下半年去了英国,这是令我痛苦的一件事。临出国前,我们见了一面,她几乎没变,我比以前朴素,主要是黑多了。她没感到意外,对我感情仍在,好好告别,好好离开。 没多久,新冠疫情爆发。随之而来的就是,我们公司也开始拖欠工资了——除了保证民工的工资,其余人的工资得都根据甲方给我们支付工程款的进度来定。而甲方(某省高速集团)打着疫情的借口,故意延后(其实,山里的疫情并不严重,工程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)。 项目总等“老人”,包括“师父”在内,似乎对此司空见惯,或是早就经历过,只讲了些“公司暂时遇到困难”、“大家要共克时艰”的话。可我理解不了,坚决认为该什么时候发工资就应该什么时候发。而在这里,甲方开始不讲诚信,不按时付款,公司也不讲诚信,不按时发钱。 我生硬地安慰自己,被拖欠的工资就权当存钱,也笑话自己,一开始的目标是做项目总经理,现在的目标是准时发工资,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大过人和狗的区别。 而杜晖比我还要愤怒,暗地里咒骂的次数不少,因为他比我更缺钱——他还得打给家里一部分。但等领导一拿编制或是涨薪的话安慰他,他立马就温顺下来了。
2020年5月,在几个大标段干过之后,公司出于大局考虑,要把我派到四川雅安的一条路去,据说那边缺一个熟练的测量员。我不愿意去,再加上已被拖欠了3个多月的工资仍迟迟没有发放的迹象,就动了辞职的念头。 虽说在这里存下了不少钱,但长期“与世隔绝”的生活让我觉得枯燥,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频频晒出的花花世界,而我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些水泥钢筋,总有种虚度光阴的感觉。更令我难受的是,偶尔和小迪视频,看着她光鲜亮丽,背后尽是异国精致的风景,而我灰头土脸,总觉得我俩的世界隔得越来越远——那些大学里没有显现的差距,在此刻一寸寸地露出来,残忍又真实。 那时她总给我说,“等我一毕业立刻就回国”,当然,说完这句,就会问及我将来会定居在哪里。我有些心慌,总是打哈哈应付着。 是啊,难道未来结婚后也常年在山里待着?——当然,这是绝大多数“土木人”的宿命,像我“师父”,一年在家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天。但我知道,小迪肯定不可能忍受这种生活,如果我继续待在山里,我俩的结局只能是分手。一想到这些,我心里还是像被剜了一刀,再者,这个工作如今连唯一的优点——工资高——也不能兑现了,这让我更加觉得憋屈。我更怕的是,再过十年,我还跟“师父”一样,依旧在山里做着最简单测量工作,拿着不能按时发放的薪水。 夜晚,我打电话给陈鑫,得知他已经被拖欠了7个月的工资了(中间补发过一点),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“你笑什么?”他在电话那头严肃地问道。 “我被拖欠了3个月工资了。” “哈哈哈哈哈哈。”电话那头,他也放肆地笑了出来。 我也应和着继续笑着,第二天就开始投简历。 我投了不少做住宅施工的公司,其中有几家都是在大城市里做项目的,甲方都是万科、龙湖一类的知名房企。我想借跳槽回归城市,哪怕坐在城市郊区的工地里吃糠咽菜,也不想继续待在山区硬挨了。当然,私心也是想着下次小迪再问我以后定居在哪里,我也好有个明确的答复。 我想叫上陈鑫一起“跑路”,没想到这货给我来了一句:“都一样,在哪儿干不是干。” 没多久,我成全了自己,告别了“师父”和杜晖,去了一家房建的乙方,位于南京,不是世界500强,也没有编制。我没敢将这件事告诉家人,因为他们总会觉得这是胡乱折腾。临走时,连“师父”也苦口婆心地劝我:“小王,你得在一家公司熬几年才能出头,你这样跳槽是犯了职场大忌。” 我只能笑笑,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去了南京以后,我晋级成为一名施工员,年薪比先前多2万。表面上看,这份工作的职责是管理施工过程、现场指挥作业、协调工程进度,其实大部分时间做的只有两件事:第一是“打灰”,就是看着工人们浇筑混凝土,一待一整天,一看一个月;第二是应付甲方和监理,甲方说话总是不客气的,检查非常多,不满意的地方也多,骂来骂去,连监理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,动不动罚钱,趾高气扬。 这工作不比在山里轻松,夜晚的天空没有太多星星,我还是住在工地,同时也有点孤独。我已完全听命于项目总经理,没有什么“师父”和搭档,只有上下级。我对于“当上项目总”这个目标开始不清晰了——因为现在的项目总经理只比我大8岁,我估计我在这里再待8年恐怕也到不了那个位置,他太年轻了,占上的坑会一直占着,项目副经理则是由另2个比他小两三岁的前辈占着——我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只能一直“打灰”。 这家公司唯一的好处就是按时发工资,在职的小一年里,工资几乎没有拖欠过。这段时间,我在业余时间考了“二建(二级建造师)”、备考“一建”,有了“二建”证书,公司把每月工资给我上浮了1000元,听说如果拿下“一建”证书,工资会上浮更多。 但我并没赶上这个行业最好的时期,这时候地产开发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,政策的打击、经济的下行、疫情的影响接踵而至,暴雷的越来越多,工程量逐渐减少。我们除了维持着基本薪资,先前承诺的奖金几乎全泡汤了。偶尔我想,比起修房子,我还不如待在上家单位继续修路呢——毕竟山河广阔,还有很多路要修,但是以后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要建。
2020年下半年,我和小迪分手了。 其实这个结果,我也早已预见到了——疫情之下,我们没有再相见过;时差之中,视频电话变少,我时间也不够多,天天被工地套牢,更不可能飞奔到英国去找她。彼此的缺点被极度放大,她不满我的种种,也是我不满她的种种。索性就分了。 分手的那晚,我一个人喝了三四两白酒,哭了,这是我第二次主动喝酒。但第二天,我还是早起“打灰”,应付了甲方领导的视察和谩骂,赔着笑。我觉得房建的甲方过于抬高自己的地位,对人极为不敬,践踏了我的尊严,再加上我受了分手的伤,很想找个地方避一避,便再次准备辞职。 其后,我和陈鑫又通了一次话,问他先前被拖欠了1年多的工资发了没有,他答复“发了”,现在是又新拖欠了3个月的。我问他要不要辞职,他还是那句话:“在哪儿干不是干。” 此时,陈鑫还是测量员,单位不但欠薪,连职位都没给他提。 这回我没笑,我想我们似乎是走上了两条路。

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专做厂房的施工方,总部在武汉,业务在甘肃。那边十分缺人,能比南京这边多赚很多钱,但多多少,没有说。于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,我连年终奖都没有等就离职了。后来听说留下的人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,聊胜于无,我没感到失落。 走了足足两天的路程才到新的工程部。那是甘肃北部一个很小的县城,人是黄黄的脸蛋,漫天黄沙,树是枯的。但工地没多大差别,以前的路桥、高层房屋换成了厂房、机房罢了,还是钢筋、混凝土、灰色的森林。 我们的甲方是某大型互联网公司,我们的任务是在西北给他们建设数据机房,存储东部的流量数据,从大局上说,这个工程叫作“东数西送”,有政策支持。 一定程度上讲,这种工程是我们这代“土木人”的“小风口”,刚兴起,缺口大,工程量足够我做三五年以上——比起疫情时代各个行业的动荡,这算是一颗定心丸。所以我也给父母坦白了来回辞职折腾的事,他们也只能接受,“男孩子多出去闯闯也没事儿”。 在这里,我仍然是施工员,主要工作还是负责“打灰”,但也开始兼搭负责起更多的职能,俨如杂事管家:现场材料是由我一一验收签证的,进度和施工工艺也由我协调,工人们的活儿由我负责组织,日报周报月报由我按时更新,就连工地上丢了什么东西,也往往是我去管。 除了以上这些,我还接了做投标文件的工作,这算个好差事,“内业(项目建设中负责工程项目资料档案管理、计划、统计管理及内部文秘管理工作)”多了,受晒就少了。 项目总经理对我做的标书很满意,各类材料详尽全面,内容美观,没多久,干脆叫我转去干工程商务,专门搞招投标——除了做材料以外,还要搞成本分析、合同起草、商务谈判。 这下反而糟了,因为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,我的肚子越来越大,逼近曾经的陈鑫的体重。有时候喝完酒后回到宿舍洗漱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我想,这才是小迪应该和我分手的时候,因为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所钟情的地方。 除了赚钱。 2021年年底,项目总经理给我发了很多奖金,我算了一下,一年的综合到手收入超过26万。项目总经理许下承诺,“明年30万,后年35万”。当然,更大的承诺是叫我接替他的位置——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非虚,他直接给我升职成了项目副经理,跳过了中间冗长的升级过程(当然,那个项目的分工非常扁平,没有一步一级的讲究,纯靠领导赏识)。 这也是我理论上离自己当初立定的事业目标最近的一次。我多敬了总经理两杯酒,喝得烂醉,年终时被他选为代表回武汉述职。他回不了老家过年,因为他是第一责任人,又在赶工期。没多久,他老婆带着孩子来找他,从武汉搭火车来的,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都在读小学,现在放了寒假,来工地陪他一个月。 看着他两个孩子,我想到,如果自己有了女友,结婚,有了孩子,多半也会这样——土木人,自古家人、工作难两全。 我又开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。
就在大家觉得我“钱途”一片光明之际,2022年初,我又辞职了。 这次辞职的原因是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,她是武汉本地人,独生女,家境不错,在通信公司做财务,长相也甜美,算是我在和小迪分开后见到的最为心动的女生了,不想错过这段姻缘。对方对我同样满意,但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离开工地,找一份武汉市区的稳定工作,早点结婚。 我答应了。 项目总经理开始很是不解,对我再三挽留,即便我一再解释,他仍有微词,认为我正是前途大好的时候,不出几年,大约可以如他一般。但说实话,我并没有觉得如他一般多么好,一样要喝很多徒劳的酒,一样要离开家人。赚了那几十万,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? 见我不为所动,总经理没再多说什么,叫我保重。家里人也对我辞掉这个工作多少有些惋惜,但我相信自己在哪都是优秀的,接下来也会有个不错的去处。 辞职以后,我来到武汉光谷,入职了一家当地的建筑设计院,民企,主要做地产相关的业务。我的职位是商务经理——说是经理,部门其实只有3个人:一个负责人,据说是老板的亲戚;一个女孩子,商务专员,负责貌美如花;还有我,负责项目投标及各类协议拟定、材料编制、成本预算等。至于升职,几乎没有可能,我归负责人管,负责人归老板管,小公司就是这样,一眼望到头。 如果说有什么盼头,那只有老板许诺的奖金。我难能可贵地得到了双休,工资算不上太低,唯一可恨的是需要加班的时间长过我先前的3份工作,晚上没有10点之前下班过。 我给女友说:“这份工作其实一般般,加班挺累的。” 女友说:“我在公司做报表,也要加班,也很累。” 是的,新的阶段有新的痛苦,什么工作又是“钱多事少离家近”呢?这份工作忙归忙,周末也能跟女友到武汉各处转转,而这里的房价也算是能企及的高度,我开始期待婚后的日子了。大概我不必像以前的“师父”和领导那样,为了职业放弃对家人的所有陪伴。 我给陈鑫打了个电话,想问问他又被拖欠多长时间工资了。 电话里他顿了顿说:“我辞职了,回老家了。” 我以为他大概回老家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去了,因为如今流行这个。他却说:“不是的,我找了个老家的工地。嘿嘿嘿。” “还做测量员么?”我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。 “是的。” 哑然。

今年中旬,大学老师邀请我回母校来做“毕业分享”,我推托了很多遍,还是推不掉。在他们眼里,我毕业3年多做了4份工,经验值得分享。但我却觉得自己哪份工都没干超过1年,实在是经验欠佳,连我都觉得是自己在“作”,周围人像我这样折腾的也不多。有同学说,是因为大家没我这样的实力,折腾不起,我也不知道这话是在安慰我,还是在“点醒”我。 做分享前,老师特意还和我交代了一些事儿,大意是,现在经济下行,土木专业的学生们就业压力大,社会舆论都不好,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鼓励,分享一些好的事情。为此,我专门写了演讲稿,尽量让大家避免一些可能会踩到的坑,但多余的忧愁,我实在也开不了口,因为说太多负面的东西没用,“土木人”只会更担忧。 临结尾,我夹带私货,分享了一点自己的故事。 “给大家讲个趣事,我以前有个女朋友,白富美哦,家住西湖,英国留学,后来我们分手了,我一度觉得是因为我去了工地的原因,所以我恨透了工地。我有段时间一直在想,如果我不是找了施工单位的工作,如果没有去工地待着,会不会还在一起,不会分手。” “其实不是的,一样会分手,现在反过来看,我们分手的原因怎么能归咎于工地呢?那会儿是我离不开工地,我靠它赚钱,不是它离不开我。当然,你要是让我说工地有多好那也罢了,绝对不好,它只能满足基本的保障和稳定,同时确实会带给你痛苦,但是社会上没啥轻松的事。” “所以去哪里、做什么工作,还是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看,不是前辈做的一定是对的或者错的,每个人都不同。就像你谈一个并不能接受异地恋的女孩子,那么你去了工地极有可能分手,做别的工作会好一些。但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包吃包住赚钱攒钱的地方,那么工地不外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” 话里话外,没那么多正能量,也没那么多负能量。临了,和老师们一起吃了晚饭,喝了酒,一些相对熟悉的老师们,也对我说了一些很拧巴的话:“土木这个专业既不好,其实也好。很辛苦,但是能赚到钱。很乏味,但是能攒下来钱。很折腾,但是不会失业。” 他们和我一样,一边说行业不好,一边又说行业好。估计其他行业的人也一样,一边吐槽着,一边以此为生。只是,我也清楚,从我2015年入学至今,土木行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,在时代洪流之下,个人选择只能是在理性和感性中不断摇摆、不断变化。 我也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确的选择。或者,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? (本文人物均为化名)
本文转载自「人间theLivings」
关注了解更多真的好故事